美国工程院1983年发布了一份《研究简报》(Research Briefings),强调新概念的价值。当专家确定有新的思想产生,不足以用传统的概念(例如机械电子)来描述,就应该发明新概念(invent new concept),这样才便于深化思想,推动概念向应用转化。
这对中国工业软件的发展很有借鉴价值。目前不少行业人士呼吁国家要支持“工业软件”,看似拳拳之心,但方法恐怕并不得当,达不到真正提升我国工业软件实力的目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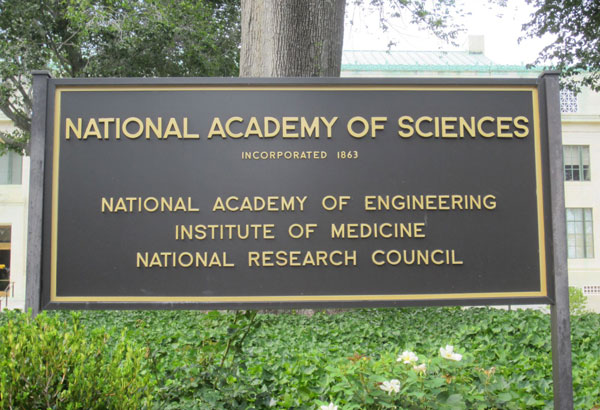
美国科学院、工程院等办公场所外景
工业4.0研究院对行业人士撰写的工业软件主题文章进行了阅读,包括但不限于赛迪顾问(王云侯、安琳)、林雪萍、赵敏、宁振波、黄培、郭朝晖、王建民和安筱鹏等撰写的公众号文章,他们对中国工业软件的发展提出了相关洞见,值得行业人士参考。
几乎所有专家都意识到,工业软件是一个“大难题”,它涉及到知识的软件表现、产业专业化分工以及市场激励机制等系统化的挑战,加上我国产业政策周期大都3-5年,不适合软件行业长期积累之需要,也影响了我国工业软件核心竞争力的积累。
一、以中庸假说看“工业软件”的意义
基于科学研究方法,工业软件缺乏足够的定义,充其量算是一个中庸假说,即通过描述性语言进行描述,没有系统的科学基础。这也是为什么行业对工业软件缺乏统一认识的缘故,只能根据经验进行判定。
前一段时间,赛迪智库撰写的《中国工业软件发展白皮书(2019)》引起了行业不小的反响,但客观的讲,作为工信部下属智库,把研究成果免费分享出来,已经是行业较大的进展,希望行业人士可以多一些包容。
本人在《清华管理评论》2018年1-2月刊中,撰写了《重新定义智能制造》,其中就明确提出了“中庸假说”的概念,主要用来说明一些不能成为范式的想法,行业人士通常用描述性语言来解释和展示。

《重新定义智能制造》一文中的插图
中庸假说是有意义的,它对于启发人们思维有价值,但是,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其局限性,那就是在满足一个完整范式演进方面具有缺陷。托马斯.库恩(Thomas Kuhn)在1970年撰写的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(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)就指出了这个问题。
对于具有较好科学素养的美国科学家来讲,这是一个常识(Common Sense)。
在2004年美国科学研究院(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)发布的《工程师2020:新世纪的工程愿景》(The Engineer of 2020:Visions of Engineering in the New Century)中,就指明了The Next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背景,当然,库恩撰写的书自然成为必读书目。
工业软件的概念比较宽泛,在西方国家提及率并不高,它们大都以具体的软件来探讨。对于中国人来讲,历来喜欢大概念,工业软件正好满足这个条件,它包含了几乎所有跟制造业有关的软件种类,例如,ERP、PLM、MES、CAx等。
当然,作为产业政策制定需要,倒是可以把概念范围做大,这样才有充足的实践案例对应,否则难以真正落地实施,例如,工业互联网就属于这样的概念。
因此,以中庸假说来看"工业软件“的意义,可以从产业政策角度来认识,目前行业人士谈及工业软件,不可否认不少人希望产业政策惠及工业软件这个品类,从而使企业可以从中获得利益。
二、借鉴美国数字孪生体2027计划
众所周知,工信部下属信软司负责软件行业的发展,如果非要说工业软件归口管理,当属该部门主管。但该部门已经把工业互联网作为主要的抓手,基本形成了“工业APP=工业软件”的定位。
工业4.0研究院观察到,由于部分企业结合到工业互联网体系,主推“工业APP”,自然不需要“工业软件”这个营销工具了,在这轮“工业软件”大讨论中,它们实际上并没有发声,其根本原因还是应该归结于它们已经是工信部推动“工业APP”的受益者。

NASA在2010年提出的数字孪生体2027计划
如果我们不考虑这样的述求,直接就未来的工业竞争来看,值得借鉴美国NASA在2010年11月提出的“数字孪生体2027计划”。
我国刚刚确定不久的工业互联网国家战略,本身就是一个中庸假说式的提法,包含了各种可能的技术及应用,不宜再推进一个同样宽泛的概念,工业软件的具体应用可以包含在工业互联网国家战略中去,事实上,工信部也是这样做的。
不仅如此,对于影响未来竞争的核心技术,本文前面提及1983年美国工程院的《研究简报》中,就指明了“设计和制造”中的计算机技术才是未来50年竞争的主战场,2006年美国科学基金会(NSF,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)提出信息物理系统(CPS,Cyber-Physical Systems)和2010年NASA提出数字孪生体(Digital Twin),都是美国未来50年竞争战略的延续。
正如库恩、佩蕾丝等人对技术革命研究的成果,一个概念或范式的形成,自身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才可能成熟。按照NASA自己2010年提出的时间周期,选择不到17年就搞定“数字孪生体”,那已经希望超出这个周期了。
中国行业人士喜欢自己发明一个概念,按照自己的理解,只需要3-5年就可以落地实施,或者至多10年时间,也要想法子产生经济效益……这是不是有些不现实?
三、把认识、应用数字孪生体作为起点
从全球技术发展趋势来看,数字孪生体作为一个开放式架构,具有较强的潜力。
以德国工业4.0发展为例,虽然在2011年左右时间,基于德国嵌入式系统优势,工业4.0把信息物理系统作为核心,但到了2015年,在美国明确放弃信息物理系统主航道,开始切入数字孪生体之后,德国也开始了切换过程。
西门子美国公司(当时为Siemens PLM Software,现在更名为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)利用信息敏感的优势,迅速调整主攻方向,启动了MindSphere等计划,同时为了弥补短板,继续采用收购的方式,把Mendix等揽入美国公司旗下。

西门子数字工业软件公司首页截图
对于正宗的美国公司来讲,这更不是问题。诸如通用电气、ANSYS、PTC、波音公司等,早就成为NASA和美国国防部数字孪生体研讨会上的常客,它们加大了相关技术的吸纳力度,并积极筹备自身产品的数字孪生重构。
大家都比较清楚,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通用电气从来没有对信息物理系统表示过青睐,其他美国公司也是如此,只是部分“灵活”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分部为了迎合中国行业客户的需要,间或提出过信息物理系统解决方案。
为什么美国人不喜欢自己发明的概念信息物理系统呢?
理由很简单,一种高度集成的工业哲学,不符合美国的利益,也不符合美国制造应用的需求。大家耳熟目详的精益制造也是同样的理由,但它的确在日本获得了较长时间的应用,并取得了较好的成就。
日本、德国这样的“小”国家,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撑工业品的规模销售,必须有大规模的市场才可以,因此它们选择装备制造为核心,培育了大量的“隐形冠军”,实属不得已为之。
中国具有跟美国一样大规模的市场容量,自然要充分利用这样的优势,选择类似美国一样的开放式架构,有助于引导日本和德国的装备制造企业进入中国的标准体系,避免被它们锁定我们的技术路径,从而降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。
数字孪生体可堪此任。

评论